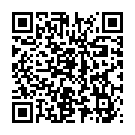首页 圣网读书 目录 A-AA+ 书签 朗读
七十、回忆黄老二三事
七十、回忆黄老二三事
——《黄德堂先生的见证》序文
黄德堂老先生是浙江省象山县田洋湖教会的一位义工。他生于一八八六年,卒于一九八一年,寿高九十五岁。我认识这位长辈已有数十年之久。从一九四八年起,我有机会到象山新桥晨光堂担任牧职直到一九五一年年终为止。在这四年的岁月里,因为和黄老所在的田洋湖教会相距不远,只十五华里。我们之间的交往就多了,相识也加深了。
黄老有许多值得我们记念和效法的特色。
他善于对未信福音的人们布道,能唱能讲,而且自己编写布道诗歌。他不会写通顺的文章,但是他写乡村布道诗歌,却使人惊异其特有的恩赐才华。他的诗歌,妙趣横溢,令人喜爱,且有感力。五十年代,我曾将他的布道诗歌收集珍藏,可惜在一九六六至一九七六的十年动乱中都失散了。
回忆一九四六至一九四七年我在象山石浦渔港养病。一天晚上,忽然得知黄老先生要在当地的一块空旷场地上对四周的居民布道,我就不顾体弱,拿了一把椅子前往听他布道。我是想从他学点布道方法的。广场上的气灯已经亮得通明。他和一些信徒先唱了几首布道诗歌以后,他就站上一张小方桌,对四周的群众传耶稣救人的初浅福音。他首先独唱了自编的布道诗歌,接着就开口向群众发出“大喜的信息”。他把“大喜的信息”译成“哈哈”。他说:“我是一个卖哈哈的人,要把平安喜乐的福音‘哈哈’告诉各地同胞们。”
广场上的听众,坐的坐,站的站,都侧耳听他。布道工作是很不容易的,要吸住不信福音的群众,安安静静地听下去,更是难上加难。但是,黄老蒙了神的特恩,与众不同,布道时富有吸引力。五十多年来,在我认识的人中,在街头布道的吸引力上,没有一个能够超过黄老的。那天晚上,我坐在群众之中留心群众的反应。当时有几个人坐在我旁边一面听,一面夹几句评论,说:“讲得真对,真好,讲到人的心窝里来了。”这已经是四十二年以前的往事。然而这一幕的情景给我印象极深,至今未能忘怀。
一次,黄老对我个人作见证说:“我献身传道以后,主要我到街头,到集市上布道。我有怕羞的感觉。于是利用毛笋壳做成面具,在面具上为一双眼睛挖二个洞,为一只鼻子挖一个孔,把口露在外面,才向群众布道。这样做了一段时间以后,胆就大了,不再怕羞了。”
黄老的另一个特色是甘心过刻苦生活而不以为苦。他的个人生活,吃、穿、用,都十分简单节约。虽然在那些年代里教会内外的人民生活都较为清苦,然而黄老则更显得刻苦己身。
最使我感动和敬佩的,是他特有的祷告毅力。每天凌晨,天还未亮,他就到山上祷告去了。有不少时候,半夜以后一、二点钟,他就上山了,而且是风雨无阻地天天登山祷告。我曾问他:“落雨天在山上怎样祷告呢?”他说:“穿好蓑衣(农民用棕树丝编织成功的雨衣),戴上箬帽,有时拿把伞子,再一枝手杖,就可以上山。到了山顶就俯伏在地,祷告直到天明,才下山来。也有时候,天未亮,祷告完毕,摸黑探路下山。有一次,山路出现奇光,一路照亮,直到山下那光就消失了。”
黄老又有一个稀奇特点或习惯。每年年底,他就离开家庭到山上祷告过年,直到正月初三才下山。在山上,他不吃不喝,专诚祷告。别人要在年终回家与家人团聚;他却喜爱到山上去用祷告与天父团聚。如果没有一个敬虔的心志和坚强的毅力,谁能做到这个地步呢?如果祈祷见不到效果,又如何能使他坚持这样的祈祷达数十年之久呢?到“文革”时,他也不停止上山灵交,直到山上听见枪声为止。
在教会里,有恩赐,有口才,能讲道,能办事的人不少。然而敬虔祈祷象黄老的人却是少而又少。这就显出黄老的可贵之处。这也是我们的重大不足之处。登山祷告不是我们每个人所能办到的。
黄老有许多特有的灵性经验。我们可以从这本见证中读到。黄老的某些预言,早就对个别人说过。一九七九年初,我从宁波到象山家乡。我遇见了他,他告诉我:几年前(正是十年文革动乱之时),神在异象中给他看二幅画面:一幅是西方的海潮,涌向祖国大陆。另一幅是数十年不来的西方人士来到中国,其中还有西教士。到今天,八十年代,我们果然见到祖国开放了,西方的潮流涌进来了。我们至少也知道英国圣公会大主教伦西博士来过了,美国的大布道家葛培理也来过了。他们都不是独自一个人来的。神在人类历史中,以“难测之法”表现他自己。黄老亲近神,神也亲近他,让他预先知晓未来之事。
教会自有史以来,不时有“奇异之士”出现。这是主特别选召安排的。他们是教会的财富是后人的榜样。
邵升堂牧师搜集了资料又编写了这本见证册子,对大家是个很不小的贡献。在不够重视祷告的教会和个人面前,尤其显得意义深厚。
我感谢编者和黄老的后代黄恩吾先生要我为这本册子写序文。我愿意与所有的读者勉励:让我们充分重视祷告的意义、价值、作用。让我们谦恭在主脚前,学习更好地事奉他。是为序。
一九八八年八月十日于浙江宁波中山西路惠政巷6号住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