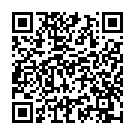首页 圣网读书 目录 A-AA+ 书签 朗读
第六章 人具有上帝形像且为被造者
发信人:Mandala(沧海当盈朱颜血山河遍染胭脂色),信区 hilosophy
hilosophy
标题:第六章人具有上帝形像且为被造者
发信站:瀚海星云(2007年04月10日04:41:05星期二),站内信件WWWPOST
第六章人具有上帝形像且为被造者
基督教的人性观与其它一切别的人性观的显然不同之处,是在于它解释人生的三方面,
并指出其中的联系。第一,在“人具有上帝形像”的教义里,它注重人灵性中的自我超
越性之高度。第二,它坚持人是软弱的,依赖的有限的,深深陷入于自然世界的必然性
和偶然性中,同时它却不承认这有限性的本身为人性中的罪恶之源。最纯粹的基督教人
性观,以人为“上帝的形像”与“被造之物”的合一体,当他处在最高的灵性地位时,
他仍然是一个被造者,而在他的自然生活的最鄙陋的行为中,他仍显出若干上帝的形
像。第三,它主张人心中的罪恶乃是由于人不愿意承认他的依赖地位,也不愿意接受他
的有限性和不安全的地位;这一个不愿意的态度,虽不是必要的,却是他所无法避免
的,并且使他更加深陷于他所想要逃避的那不安全的境界中。
我们分析基督教人性观中的这三个成分时,一方面要追索基督教信仰中说明这一个圣经
教义之逻辑的各种解释,避免它们与其他的和本身相反的人性观相互混。另一方面,我
们为要保证基督教的观点必须努力对基督教人性说之解答人生问题的贴切性加以衡量,
而这问题已为其它各种人性说所扰混了。
第一节圣经的人性观
圣经说人是按照上帝的形像造的,这当然不用心理分析来发挥它。圣经中的心理学从来
未曾有过希腊思想中的那种心理分析。正如早期的希腊思想一样,最初圣经对于灵与魂
二者未作小心的分别。Ruach与Nephesh两字的意义都是“气”或“风”,在旧约中二字
是通用的,表明希伯来观念中的肉体与灵魂为一体,而不曾表白灵的超越性。希伯来人
相信“魂”(Nephesh)是在人的血中,足证他们对灵肉有合一的看法。但ruach一字渐
次被认为是人对上帝发生关系之心灵机构,乃与魂一字有别,而魂乃成为人生命的原
理,具有“灵魂”(新约的psyche)的意义。圣经常说到诸先知为上帝的ruach所感动
(注一)。新约中的psyche与pneum二字之别,实际上与旧约后期各书上的观点是一样
的,pneuma一字所表达的概念是与ruach一字一样的。因之乃有“灵”与“魂”二者之区
别。可是这种区别。并非绝对的,因为“灵并非在魂之外。……灵与魂是不能分开的,
这与灵魂和肉体的分别不同。灵与魂可以分别,但不可分开;当它们分别的时候,灵就
是魂的原理”(注二)。虽然,灵与魂的区别并非绝对,然而新约中所用的灵
(Pneuma)一字(与希腊哲学中的那个更理性的名辞心智nous不同),是那么清楚地将
人性中的神性表达出来,以致好些解经的人主张(虽不能算为确定的)说,保罗以为以
性中没有自然的灵,灵无非是上帝所特赐予人的(注三)。保罗虽然有时用“灵”一字
表明人的天然禀赋,我们得承认,他的心理立场总是把灵与肉体(sarx)对立起来,这
个立场就是由他的救恩教义而来的,而“灵”的意思不只是指着一种天赋才能,“肉
体”的意思也不只是肉体,而是罪的根源。所以圣经上的心理学立场,除去创世记人具
有上帝的形像之说,就不足以立定后来基督教人性说的完全基础,但与后来基督教的各
种人性说之一般轮廓是相吻合的,因为它在灵魂与肉体,或魂与灵之间都没有加以深刻
的区别,它也没有用希腊哲学的理性观念去界说灵。它对那灵魂与肉体合一的希伯来看
法也不**,却在另一方面把灵当作是人与上帝相交往的工具。
这种对灵的看法,由于后来基督教的神学企图说明“上帝的形像”而更加显明。特别是
在早期受柏拉图学说强烈影响下的希腊教会,和中世纪末期,即亚理斯多德与奥古斯丁
及圣经平分对神学真理的最后评判地位期间,有些人企图以不超越于亚理斯多德认人为
理性之物的范围来说明“上帝的形像”,然而即在接受柏拉图与亚理斯多德影响的各种
基督教思想中,仍提示“上帝的形像”乃指人倾向上帝的意思,即暗示着按基督教之了
解,人的超越自我的能力是无限的(注四)。
奥古斯丁对这个教义,和对其他的教义上一样,是了解基督教人性论之充份含义的第一
个神学家(注五)。奥古斯丁一生受新柏拉图主义的影响,以至于似乎是以纯粹理性的
辞语界说上帝的形像。他说:“并非人的身体,而是人的心意,才是按照上帝的形像造
的。让我们以那与上帝相近似的心意去追求上帝,从祂自己的形像中去认识造物主”
(注六)。又说:“只有人的灵魂,即那理性和心智的灵魂,才在它的永恒性中具有造
物主的形像。……虽然理性与心智有时在人的灵魂中潜藏不露,有时表露很少,有时表
露较多,然而人的灵魂不是别的,只是理性的和心智的。因此,倘若说人的灵魂之按照
上帝形像而造,是在乎它能用理性来了解并瞻仰上帝,那么,自从那伟大奇妙的性质开
始存在的时候,不问那上帝的形像是显露于表面或几乎没有表露,不问它模糊残缺,或
是光华美丽,它总是存着的”(注七)但是奥古斯丁所谓“理性的与心智的灵魂”,他
的意思显然不只是说那是一种理解的能力,或是能构成“普通概念”的才能。这里我们
看出他用新柏拉图的思想来支持他的圣经信仰,因为普罗提诺所说的“心智”(Nous)
乃是表明人的自我认识和省察的能力。而奥古斯丁的主要兴趣乃是人灵性中的超越性甚
至能超越自我。人的记忆力既表征着人能够超越时间,甚至超越自我,所以奥氏对它特
别重视,它说:“当我进入记忆的领域时,有的事我一要求就有了,另一些事却需较久
的搜寻,好像是从深藏之处去将它提出来。然而那进来的并非那事物的本身;只有那所
感觉到的印象。因为即令我是在黑暗与幽静之中,在我的记忆里,只要我愿意,就能生
出颜色来,……虽然没有闻着什么,却能辨别百合花与紫罗兰的气味。……这些事是我
在广大的记忆领域中所作的。……在那里我可以遇见我自己,并追忆我在何时何地作过
什么,而且是以何种心情作的。……在这同一的记忆的领域中,我常不断地将过去的
事,来与我所经验到和所相信的联系起来成为新鲜事物;然后再推断将来的行动,事情
与希望,当作现在的事思考它们。我在那一个伟大的,储藏了许多伟大事象的心智中,
对自己说我要作这作那,这或那就成就了。”
人的超越时间过程之才能及人的自我决定与自我超越最高的能力,都在奥氏的心中引起
了一种惊奇之感,使他深信自我的限制毕竟是在自我之外。他以下面的话结束他称颂记
忆的诗章:“上帝阿,记忆力真是伟大,非常的伟大;是一个伟大无量的闭宫,谁曾探
悉它的底蕴呢?然而它是属于我本性的能力啊!我自己并不能领略自己。人心岂不是太
狭隘,不足以包含它自己么?倘若它不能包含自己,又将置之于何地呢?岂是在人心之
外而不在人心之内吗?要不然,如何不能领略它自己呢?在这一点上,有一种奇妙之感
令我惊奇,抓住我的心。”奥氏再三回到这一种超越自我的能力方面,认为这是他的超
越能力中的最显着的一方面。“当我想到我的记忆时,记忆本身是藉它自己而来,也在
它自己身上出现;但当我想到‘忘记’之事,于是记忆与忘记两者都出现了。”……
“上帝阿,记忆力是伟大的,伟大得可怕,乃是一个渊深无底,包容一切的复杂物;记
忆即是心意,也即是我自己。上帝阿,我究竟是什么呢?我的本性又是什么呢?”
奥古斯丁于思索人超越自我的性质为何等奥秘时所达到的结论,对于了解人生的宗教问
题是极关重要的。他结论说,那超越的能力将他置于一切事物之外,使他只有在上帝里
面才能找到一个归宿:“我跳到这边,又跳到那边,尽我所能,终无止境。即令在这必
死的生活中记忆力是如此伟大,生命力是如此伟大,我的真生命,我的上帝阿,我将怎
么办呢?我要越过这所谓记忆的能力;是的,甜蜜的光辉阿,我要越过这能力,好来亲
近你!……我将从何处找着你呢?我若不凭记忆去找着你,那么,我就不能将你保存在
那记忆中。倘若我不记得你,我又如何找着你呢”(注八)。
最后的那些问题是特别重要的,因为它们将奥氏心中的新柏拉图派与基督教思想的分水
线标明出来。一个新柏拉图主义者的奥古斯丁想从自我意识的神秘中去追求上帝,在他
早期的着作中,有些地方他还是几乎把自我意识当为神明,他说:“进入你的自我之
中;进入你心中的隐密之处。倘若你离开自己很远,你又如何能接近上帝呢?”(注
九)。又说:“若你发现本性是可改变的,则你要升超于自我之上。但当你超越自我的
时候,就当记得你是升超于理性的灵之上;所以当努力达到理性光辉的来源”(注
十)。我们必须承认,奥古斯丁对人性灵的奥秘与神奇性性所显示的兴趣,并不仅仅是
从基督教的透识中得来的。奥氏见解之如此重要,乃是因为他能采用神秘主义和基督教
信仰之共同长处:他懂得人灵性之高深处,是深入于永恒里面;为要了解人性,人之具
有这一种向上能力,较之他之具有构成概念的理性能力,更为重要。那后一种能力不过
是从前一种而来的。后者不过是对世界的一种平面的展望,是由于人的灵性高度才有可
能。
然而奥古斯丁的圣经信仰足以拦阻自己,使他不至于与神秘主义者同认自我意识为神。
人的各种能力都指向上帝;而却都不能了解祂:“单就人性来说,在人里面没有比心智
或理性更可贵的。但那希望在生活上蒙福的人,就不当依循心智与理性生活;因为那
样,他的生活就是遵循人的意向,其实他所应遵循的却是上帝的旨意”(注十一)。他
又说:“我们说到上帝。你若不了解上帝,有什么可稀奇的呢?若是你能了解,祂就不
是上帝了。……心灵能在若干程度上接近上帝,乃是一个最大的恩赐;但是要了解祂是
完全不可能的”(注十二)。在这一点上,奥氏对基督教启示的着重,足以救他脱离神
秘主义的最后的危险。人生的指向是超乎本身之外的,但它不能以为自己可能成为那超
越者。若是那样,就犯了人类的基本的罪。因此,人只有靠着信仰作为了解的前提,才
能了解他所处的整个地位。“虽说除非人有相当了解,他不能相信上帝,然而藉着他的
信心,他可以了解更大的事。有些事情,除非我们了解就不能相信,但另外有一些事
情,除非我们相信,我们就不能了解”(注十三)。
若将奥古斯丁早期所有的新柏拉图主义的弱点除去,我们就得承认,再没有别的神学家
对人与神的关系和距离的说明,比他的更能折服人心的了。一切后来关系人性中上帝形
像之特性的说法,都渊源于奥氏,特别是已脱离了幼稚的理性主义之威胁的那些主张
(注十四)。
基督教神学在奥古斯丁思想的影响之下,始终一致地以灵魂中的理性功能来解释上帝的
形像,同时于诸般理性功能中且包含着认识上帝的能力,以及在尚未为罪所染污时靠着
顺服造化主而得到福泽及美德的功能。加尔文说:“所以灵魂虽然不是人的整体,然而
说人是上帝的形像若是指着灵魂而言,是没有谬误的。不过我还是保留我所立下的原
则……所谓上帝的形像是指人性超过所有其他动物的一切优点而言。这一词语,乃是指
始祖亚当在堕落以前具有的完全品性;这就是说他有正当的智力,有理性所控制的情
感,和其他一切管理得宜的官感,并因天性上所有这些优点,是和他的创造者的优点相
类似(注十五)。
这里当注意的乃是加尔文以人性的卓绝构造和人的原有完全品格(现在已丧失了)两者
来界说上帝的形像。加尔文说得很清楚,所谓灵魂的理性,是包括奥古斯丁所分析的意
志的自我决定与人的超越性而言;加尔文说:“上帝使人的灵魂有分辨善恶,分辨义与
不义的心,藉着理性的亮光,又能分辨那些是应当追求,和那些是应当避免的……上帝
使意志隶属于这个官能,作为选择的根据。人的原始状态是靠这几种优美的官能,而成
为高贵的;他具有理性,了悟,谨慎和判断力,不只为管理今世的生活,亦使他可以上
达于上帝而得到永恒的福乐”(注十六)。加尔文对于希伯来人和圣经中关于人的整个
本性,身体与灵魂的一体观点也未忽略,他说:“虽然上帝的形像主要的还是在思想和
心灵上,或在灵魂和灵魂的智能上,然而人身无论那一部分,多少都为神的荣光所照
耀”(注十七)。
虽然改教运动大体上说是一种恢复奥古斯丁所主张的人性观和上帝对人的计划等教义的
运动,可是我们不能说马丁路德对奥氏的上帝形像说曾加上了什么重要的见解。路德所
关切的,乃是重行建立奥古斯丁的原罪论,以反对天主教的半伯拉纠思想,他所有对上
帝形像的一切解释,都表明他是热烈地要证明,不管人性中上帝的形像原是怎样,而今
已是丧失了:“所以当我们企图讨论上帝形像时,我们所说的是一件人所不知道的事,
这个上帝形像不但是我们所没有经验过的,并且与我们生平所经验到的是相反的。所
以,我们现在所留存的‘上帝的形像’只是话语而已。……但是在亚当心中有一个光明
的理性,对上帝的一种真认识,一个爱上帝和爱邻舍的正直意志”(注十八)。路德所
说的是间接地而非直接地证明着,自然神学不能不主张一种上帝形像说,和主张人类堕
落以前有一种完全境界,这样的说法是由于人性中倾向于求超脱他目前的不完全和罪的
境地,并忖想着一种人必须实现的完全境界。路德虽然坚持“表现在人身上的上帝的形
像已被罪所模糊**了”,而且是“如此的污秽不洁”,因此甚至在人的思想上亦不能
“了解它”,然而路德却进而以它与目前处身罪境中的人之对比去了解并说明它。他
说,虽然我们只“保存了一个名义和面像,即是那原有的控制力所剩下的虚名――它的
实质是几乎完全丧失了……然而我们之知道并思想到这事,仍然是有益的,好使我们羡
慕那将要来的日子。”他从反面来说明上帝形像的结论,即是上帝的形像是胜过人的
“灵魂,记忆,心智和意志能力”的。他认为即令是经院派所说“人的记忆是富有盼望
的,心智是具有信心的,意志是具有爱心的”的那界说,仍然不够。“上帝的形像是与
此不同的。……亚当身上所有的上帝的形像,乃是一种最美丽,最优越,最高贵的上帝
的手艺;他的心智是最清明的,他的记忆是最完全的,他的意志是最诚实的,他也有最
可爱的安全之心,既不惧怕死亡,也没有任何焦虑”(注十九)。路德以极其夸张的说
法,强调人类堕落以前的境界是如何完全,显然是要加重人类目前的罪恶,悲惨,及死
亡的处境,若将他的说法与奥古斯丁和加尔文的说法比较,路德的思想是如此的不贴
切,所以在解释基督教信仰中上帝形像那个概念的真正意义上,他是没有什么贡献的。
最多只能把他的话当作是证明,在基督教信仰中比在任何其它人生观中,那把人的地位
衡量得更高,把人的德性衡量得更严的观念,已经多少丧失了其中的对立性。在路德的
身上,基督教的“良心不安感”是爆发得太猛烈,且是如此不妥协地针对着天主教经院
主义的道德作风,以致模糊了对人类灵性结构的正确观点,一缺少这种观点,人类的良
心不安感就毫无意义了。
我们不须再作历史的分析,总括地说,圣经中“上帝的形像”这一概念,对基督教思想
(特别是从奥古斯丁以后,除了受强烈的柏拉图或亚理斯多德思想影响的时候)之主张
人性虽包含着理性才能,却也有超理性才能的解释,颇有影响。近代分析人性最杰出的
非神学思想家亥得革(Heidegger)曾简括地说明基督教信仰中的这个着重点乃是人的
‘超越观念’,那是说,人是一种超乎他自己本身之物――他不只是一个理性的被造者
而已”(注二十)。席勒(MaxScheler)依据圣经的传统,提出“灵性”一辞,与希腊
字的nous对立,来表明人性中的这一种特别品质与才能,因为必须用“一个字,虽然包
含着理性的概念,却须于思想观念之外,也含着一种了解原初现象或意义概念的特殊能
力,且具有一种为善,为爱,为悔罪与虔敬而有的特殊情感与意志能力。”他更宣布
说,“人性和那可以称为人的卓绝品质的,乃是超乎心智与那决择的自由的,即令有将
人的心智与自由提高到无可再提的可能的话,仍然不能达到那种卓绝的品质。……光就
技术的智能来说,艾迪生(Edison)和一只聪明的猴子间的差别,只是程度而已,即令
那程度是很大的。反过来说,人的灵性能超越乎它本身的生机体地位,将整个在时间和
空间中的宇宙,连同它本身也包括在内,都成为他认识的对象”(注二一)。
席勒所说的自由,乃是一种胜于(在某种意义下也是逊于)那寻常为哲学神学所注重的
“自由选择”。所谓人的自决,不只是说他能超越自然秩序,对自然过程所提供的加以
选择,而是说他能超脱他的自我,去选择他的总目的。在这一个自决的大业中,他面前
摆着无限的可能性,人所当达成的目的只有那最后的真实才能加以限制。然而人仍然是
一个被造者,他的生命确是被自然所限制的,他的选择不能超出这被造世界所已定的范
围。人类自由的这一个矛盾,祁克果曾简括地说明:“人类处境之实在情形恰是人之选
择与决定和被选择与被决定是同时兼有的。我所选择的不是我所能决定的,因为除非它
是被决定了的,我即不能选上它;然而它若不是由我的选择而决定的,我就不能真正地
选它。它存在着,否则我就不能选择它。反面说它不存在,只因为由我的选择才成为事
实,不然我的选择就是幻觉。……难道我要选择那‘绝对者’么?‘绝对者’是什么
呢?我即是我本身的那个永恒人格。……但这个我自己又是什么呢?……他乃是一切真
实中最抽象也同时是最具体的。他即是自由”(注二二)。
祁克果对人的矛盾的这种卓越说法,却一半因他将自我与“绝对者”及“永恒人格”视
为一体而混淆了。在基督教的信仰中,基督既是启示上帝的品格,也是启示人的本质上
的性格(祂是第二亚当)的,这足以证明,人只能在神的品格里找着他的真实的常范,
然而人仍然是一个被造者,他不能,也不可期望充作上帝。那作为人的常范的上帝,乃
是那启示在人类历史中的一个品格上的上帝,即是启示在基督里的。基督既是一个历史
中的品格,同时也是超历史的品格,祂的生命超越一切历史的可能性,同时也与一切历
史上的努力相关连,因为一切历史的目标,只能以超历史的观点说明。若只从纯历史的
观点说明,则一切历史目标所包含的,就只是自然和历史中的一些有限的事,对人的灵
性就立下了一谬妄的限制。基督教信仰中的这一方面的基督观往往不为自然主义者的基
督教信仰所了解,他们是以“历史上的耶稣”来作为人生的常范的。这一派人的信仰不
了解人类所有的自由之整个地位,所以他们不能领略历史性的人生必须有超历史性的常
范。
基督的完全的爱既在历史过程中出现后,以十字架为终结。所以祂的生活就是超历史性
的,不是说它立了一个非历史性的永恒作为人生的目标;而是说它所包含的爱乃是历史
的顶点和终点(注二三)。
人是自由的,他能超越自我与宇宙,同时他对宇宙的意义若不能找到一个超越宇宙的根
基,就不能构成一个有意义的世界。意义的问题乃是宗教的基本问题,它是超乎那寻常
探索万事万物的相互关系的理性问题之上,正如人的灵性自由超越他的理性才能一样
(注二四)。
若不引用一个超越宇宙的意义原则来作解释,这个问题是不能解决的。若用一种生机或
次要的统系原则来作为意义的原则,即是陷入于偶像崇拜。这样他是将一种有限的或偶
然的抬高到了神的超越的地位上,是把一种本身仍需要解释的东西,当作一个意义和统
系的终极原则。这偶像崇拜的明显的例子,即是那些以一个自然或历史生机的中心,如
同部落或民族等的生存,来统贯宇宙的意义,而这些部落或民族的生命却显然是偶然而
非终极的。采用一种次要的意义与统系原则来作为终极的原则,这虽较为隐蔽,却仍然
是一种偶像的崇拜。自然因果说即属于这种次要原则。只拿自然因果原则来领略宇宙的
意义,就等于是以机械性的系统去了解世界,这样,人类意识中所表现的自由就没有地
位了。种种理性原则的体系也只是另一些似乎较高,却仍然是不洽当的意义体系。把理
性当作最后的意义,即等于是尊奉理性为神。这就是崇拜偶像,况且理性与逻辑的定律
都不能完全了解宇宙的整个意义,这一事实,由于人生与历史都充满着矛盾,不能以理
性的原则解决,可得佐证。况且一个超越本身的心智,决不能合理地使自己成为解释的
最后原则,并以之说明心智对宇宙的关系。人之超越自己的这事实,必然领人去追求一
个超越世界的上帝。奥古斯丁曾很准确地解释了这个道理,他说:“我跳到这边也跳到
那边,就我所能见到的,那是无终极的。……我要超越我的这一个称为记忆的能力;是
的,我要超越它,我才能接近你”。
虽然我们所藉以领略上帝的宗教信仰不能与理性冲突,那即是说,虽然意义的终极原则
不能与理性那种次要的和谐原则冲突;然而另一方面,宗教信仰也不能隶属于理性之下
来受它的裁判。否则当理性追问宗教信仰中的上帝是否合理的时候,它这样问是已经含
着一个否定的答案了,因为这是理性把自己当作上帝,它自然不能容许另一个上帝。当
理性对宗教下一个判断时它总是说,宗教信仰中的上帝在本质上是与理性所构成的上帝
相同的,只有一个区别,即认为宗教信仰的领略方式是粗劣的,而理性的领略方式却较
为精纯。
实在情形乃是:人既是按上帝的形像造的,正因为人性中有那种“上帝的形像”的品
质,所以人不能以人的想像所产生的上帝为满足。因他能超越自我,他就能充份地认识
那凭他自己想像所构成的,并非上帝。这并不是说他不会犯拜偶像的罪,凭自己的想像
去制造上帝。人常陷于拜偶像的罪中,因为人只想到他的自由权能与尊严,而忘记了他
的有限。然而神秘宗教之力求逃避那拜偶像的罪,且图克服以有限性的说法来说明上帝
的过失,即可证明人性中有超越性的远见,足以体会那拜偶像的罪。
在神秘的灵性中所显示的,人能意识到拜偶像的罪,而且对之感到不安,这能力当然并
没有解决何以人在一方面超越自我,而在另一方面是有限性的这个问题。若没有基督教
信仰的假设,人类为要逃避偶像的崇拜,就要否定人生与否定宇宙了。他们若不是拿一
种相对的生机或制度来当作意义的绝对原则有即是否定整个现象世界的历史生存,因为
它是相对的。
为要了解基督教信仰对人的自由与人的有限这问题的对立看法,所以必须将人为被造
者,和人具有上帝的形像这两种教义作平行的研究。
第二节论人为被造之物
基督教之视被造世界为善良的,是根据创世记中的一句话:“上帝看一切所造的都甚
好”(创1:31)。这一个教义当然并不是光靠创世记上这句话作为根据。整个圣经对于
生命与历史的解释,都是假定那被造的世界,那有限的,有依赖性的世界,并不因它的
有限性而是邪恶的。
我们必须承认若没有创世记中这一句话,基督教信仰在某些时期可能有屈服于二元论及
否定宇宙之学说的危险。然而基督教对本身信仰的核心亦未曾全然无知,它仍然明白世
界并不因其有限性而为邪恶,肉体也并非人类的罪恶之源,那具有特殊个别生存的个
性,并不因它是与浑然的整体分开而为邪恶,而且死亡虽造成恐惧,给了恶一个机会,
然而其本身并非邪恶。
圣经的看法乃是:人的必朽生命之有限性,依赖性和缺欠原为上帝的创造计划,对这事
实,我们必须以谦卑敬虔的心来接受。圣经中表达上帝的庄严和荣耀最美丽的一段,即
是将人生的短促有限来对比神的庄严:“凡有血气的尽都如草,他的美容都像野地的
花。草必枯干,花必凋残……惟有上帝的话必永远立定。”个人的集体的和民族的生
命,虽常给人一种超乎个我的永恒性之幻觉,却同样被那位作者认为是处在同一的有限
性中:“看哪,万民都像水桶的一滴,又算如天秤上的微尘……万民在祂面前好像虚
无;被祂看为不及虚无,乃为虚空”(赛40章)。圣经从生命和意义的中心之远景来透
视人生的残缺性,使每一残缺的部分,都与上帝旨意中的整个计划发生联系,所以不算
为恶。恶之来乃是因那残缺性的分子欲藉自己的智慧来了解整体,并靠自己的能力来实
现完全。圣经中的上帝观总认为上帝的旨意与智慧必然是超过人对祂的正义和意义的一
切解释,否则,祂就不是那包括万有的意义中心,仍然而能了解那似乎是混乱的现象,
而使之变为整个的和谐。这就是约伯记的意义。约伯想拿人的标准来测度上帝的正义,
他受挫折和严重打击,至终因上帝将一切人所显然不能了解的宇宙庄严和奥秘显示给
他,而完全克服了他。神的种种理由在下面具有挑战性的问题中提出:“当我为世界建
立基础的时候你在那里呢?”这问题终于使约伯悔改顺服地说:“所以我所说的,是我
不明白的;这些事太奇妙,是我不知道的。……我从前风闻有你。现在亲眼看见你。因
此我厌恶自己,在尘土和炉灰中懊悔”(伯42:3,5,6)。
耶稣曾将人的依赖性与软弱和低极的被造之物相比较说:“你们那一个能用思虑使身量
多加一肘呢”(太6:27)。我们要注意,这个说法是耶稣分析人类情况的一部分,目的
为要说明人与下层被造之物都生存于上帝的护佑中。我们不妨在此顺便提出本书以后所
要阐明的人生罪恶之由,提出耶稣所说的那句话:“所以我对你们说不要忧虑”,这句
话包含着圣经对人之有限地位与罪的关系之全部卓越观点。不是人的有限,依赖与软
弱,而是人对这些缺欠的忧虑,才诱转他陷于罪中。
新约中对于人与被造的世界之短促与无能,比旧约所记载所的要少些,但它的着重点并
没有改变,只有一个例外往后要提到。如在希伯来一章中,它始终着重于一切暂时存在
物的短促与依赖性,来对照上帝的庄严与永恒性。但是这个对照总不是一个道德的对
照。被造的世界乃是一个善良的世界,因为它是上帝所造的(注二五)。
至关重要的,我们当认识基督教所相信的被造世界是善良之说,这教义是着重人的有限
性而并不以之为邪恶。圣经中对被造的世界与造物主,对人的依赖性与欠缺,和神的自
由与充足之间的对立观点,乃是绝对的。但是这一个对立,并不认为被造的世界,因各
种各色的存在物之个别化与特殊化而成为邪恶的。圣经观点不像新柏拉图主义所说的,
这个世界乃是神的原有永恒和统一性腐败的结果;也不是如佛教所主张的,一切具有缺
欠和依赖性的生命,因它的欲求与苦痛而变为邪恶的(注二六)。
基督教的创世论对人性观所以有意义,乃在于它的个性观。基督教以个人为一个具有无
限可能性的被造物,这可能性不能在人的有限生存中完全实现。而人得救也不等于是他
的被造地位之完全取消而使他进入神性的意思(注二七)。在另一方面,虽然个性不因
它的有限而被认为邪恶,但它的有限性(包括心智有限性)是毫不含糊的。那自我虽在
它自我意识达于最高度的时候,仍然是一个有限的自我,它若企图超越个性的限度而幻
想达到普遍性(如理想主义的哲学所企图的),就算为罪。它总是一个自我,它总是为
它的生命忧虑;它的普遍的展望受制于它的肉身。虽然它旷观整个的世界,并以为它那
部分地超越肉身限制的特性,使它可望为神。事实上它仍然是一个很有倚赖性的自我。
这并不是说,当人知道了这种解释之后,他就不至于像别的生物之犯那僭妄的罪。基督
教的思想很有一部分是受柏拉图观念影响的;即或不然,人的骄傲,甚至都要在那抑制
它的基督教信仰里面表现出来。但是我们当认识,圣经所表示的真实基督教信仰是不应
受唯物主义者与自然主义者指控为“理想主义”的。因为基督教知道人的自我是有限
的,而且是陷入于自然和历史的相对性中。按照基督教信仰的根本观念,即令自我意识
伸展到最高度时,自我仍然是一个有限的必死之我。在这一方面以及在别的方面上,祁
克果对于人的自我地位之真谛,比较任何近代(或许连他以前)的神学家,有一种更确
切的解释。他说:“决定自我的因素乃是意识,即是自我意识。意识愈多则自我亦愈
多,意识愈多则意志也愈多;意志愈多则自我又更多。……自我是一种在意识中以那与
本身相关的‘有限’和‘无限’之间的综合。这综合的目的乃在造成自我,而这一个目
的只能在与上帝有关系时始能达成。造成自我的意义即是成为具体的我;而具体的我之
达成既非受限制,亦非不受限制,因为那必须成为具体的,乃是一个综合。所以那发展
的过程是:自我在永恒化中逃避自我,在现时化中又返回到自我二者永不止息地交替往
还”(注二八)。
我们却不能说,基督教的思想与生活是始终保持着圣经中的卓见,承认自我有限性,依
赖性,和缺欠为人的基本性格,而且在本质上是善的。反之,基督教从开始即将理想主
义和神秘主义的一些错误,包括它们各种对人的错误估计,纳入自己的思想中,至今未
能排除。在奥古斯丁以前的数百年中,控制基督教思想的最伟大的神学家俄利根,因倾
向于将柏拉图思想并入基督教信仰中,故认为人的“堕落是由于他在生前已背弃了上
帝,因而受那陷于变迁和有限性中的惩罚”。他认为人的性生活既是这变迁的结果,所
以是罪的特别象征。值得我们注意的,整个希腊时代的基督教观念,都把性生活看为罪
的结局和罪的特别象征,不只因为**被当作是一种显然的肉欲;也因为**显然是我
们有限的生存所必不可少的;因为若不是男女彼此结合就都不完全这一事实,乃是人生
的缺欠和彼此依赖的最显着例子,也是那抽象的理想人性受自然情势与必然性的支配与
限制的一个显然例证。以两性生活为人类堕落的结果,往往表现在希腊化基督教的教义
中,尤以各种异端的思想为甚(注二九)。希腊正教神秘思想的近代杰出人物伯尔介夫
(NikolaiBerdyaev)对性生活也有同样见解(注三○)。敦司苏格徒(DunsScotus)
亦然。
奥古斯丁时代以前的基督教往往认为罪与邪恶是在于有限世界的变迁和有限心智的无
知。殉道者游斯丁(JustinMartyr)说罪乃是无知;而革利免则界说罪是由于“物体的
软弱”和“非出于意志的无知冲动”。女撒的贵钩利(GregoryofNyssa)力图调和希
腊思想与圣经对邪恶本性的看法,却未甚成功。他说:“将人身上的倾向情欲的过失指
归于那按照上帝形像所构成的人性是不可的;但因为兽性先临到了世界,人类因为上面
所提的那个理由,就分受了它们的天性(指**而言),也就同时分受了它们天性中的
一些其它的特性。”……“所以人类的爱好淫乐,乃是因为我们是同无理性之被造物一
样造成的。”在这一点上,贵钩利又补充一个圣经的意思:“而这爱好情欲的罪又因人
类的犯罪而增加,由情欲而起乃成为众罪之源,却是我们在动物中所看不见的”(注三
一)。贵钩利所有关于灵魂与肉身关系的那种十足柏拉图化的思想,很明显地表明于他
的纯金与混合金的比喻中,那一类的比喻从当时到现在,常见于二元论的基督教思想
中:“正如那从杂金中炼取纯金的人,不只是要熔解那成分低劣的杂金,而且也要将其
中所含的纯金加以熔解,直到其中所含的杂质消蚀之后,才留下那纯金;照样当邪恶要
在炼火中被消灭时,那与恶联系在一起的灵魂,也必得投在火中,直至一切物质的混杂
物都被烈火歼灭”(注三二)
爱任纽对于有限性及灵魂之关系的见解,由于他相信须摆脱自然的有限性以使灵魂自由
这一点可以看出:“我们怪上帝为何不在开始的时候即造我们为神,却要我们先做人后
来才变为神。……祂知道人类的软弱;但凭着祂的爱心和能力,祂必管束祂所造的。因
为人的本性必须先表现出来,然后以那永生不朽的来克服那必然朽坏的,最后才能叫人
满有上帝的形像,能辨别善恶”(注三三)。带着希腊色彩的基督教与那些在基督教以
前所有希腊的各种神秘宗教,和追求永生不朽的宗教有许多相类似之处。那一个时代的
基督教常以基督战胜死亡,使人永生成神,作为“得救”的定义。
圣经中虽未将有限性看为恶,但却看死亡为恶。保罗的神学思想即以死为罪的结局。关
于这观念与那认有限性即罪性的希腊思想之不同处,奥古丁说得很好:“我们是因罪而
死亡,并非因着死亡才有罪”(注三四)。正是对保罗的话的适切解说:“罪从一人入
了世界,死又是从罪来的”(罗5:12)。
虽说“罪由死亡而生”与“死亡由罪而来”其中有很大的差别,但保罗的解释死亡,往
往使人藉口来作为二元的说法。是否保罗始终是说肉体的死是罪的结局,也不十分清
楚。然而他常用“死”来象征灵性的死亡,例如他在以弗所二章一节中说人“死在过犯
罪恶之中”。况且保罗所说“死的毒钩就是罪”(林前15:56),很难解说他的意思就
是:死是罪的结局。其实,这似乎与圣经中对罪与死的一般看法相符。圣经并不以死
亡,不安,和依赖的本身为恶,只是当人在骄傲中想藏匿他的死亡性,并想藉着他自己
的能力去胜过他的不安,以建立他的独立自尊时,死亡才成为恶的机会。当然,最理想
的可能即是那具有完全信心的人之不惧怕死亡,因为他深信:“无论是生是死……都不
能使我们与上帝的爱隔绝,这爱是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的。”然而因不信乃是罪的本
原,所以有罪的人不能平心静气来预测将来。因之罪乃是“死的毒钩”;那毒钩的显明
记号就是惧怕。
不管圣保罗对死一名辞的象征用法以及他在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上的沉重解释如何,可能
保罗仍旧是随从当日的拉比们的教训,相信死乃是亚当犯罪的结果(注三五)。人常假
定保罗只是解释创世记所载上帝咒诅那堕落的亚当的说法。但是当注意的,创世记只默
认人是必死亡的,而未将死亡列在亚当所当受的各种刑罚中(注三六)。
确然,那“你本来是尘土”的话只能当作是道破一件事实,并不是指将来的刑罚。那
“你仍要归到尘土”的结论,可以解释为含有刑罚的意味。若是这样解释,它的意思即
是说,人虽由尘土而来,但他若不因为犯罪,并不必要归回尘土。
这正是基督教正统信仰的解释。亚他那修(Athanasius)把这个教义以古典形式说出:
“按照人的本性,他诚然是必死的,因为造成他的各种成分都是本体的。但是因为他与
那‘有本体’的上帝相似,他可以排除必朽而归于不朽,正如智慧书上所说的,‘能留
意于神的律法,即是不朽的保证。’既然是不朽,即是永生,他将来就可能永生如上帝
一般;这一点圣经上也曾表明,即如所说,‘我曾说你们是神,都是至高者的儿子;然
而你们要死,与世人一样,要仆倒像王子中的一个。’……但人却脱离永恒之事,听魔
鬼的话去倾向那必朽之物,就造成他们必朽之因而归于死亡;正如我前面所说过的,按
照人的本性他是必朽的,然而因着由恩典所领受的道,他们若是保持完全无罪,就可以
避免本性中的必朽”(注三七)。
这个解说的好处,是它能解说人生的基本矛盾:即是人虽陷于有限之中,却也能超乎有
限之上。然而因它以为人若没有罪的纠缠,即可倚靠自己超脱死亡,就把那一个道理混
淆了。这种说法将人与自然界的根本关系弄模糊了,它必假定罪将死亡带入整个的自然
才有意义。但这样一个假设几乎是与希腊人相信自然与有限本身即是邪恶的观点相同。
这样看来,那札根于保罗神学思想中的基督教正统教义,虽然是以死为罪的结局,而不
以罪为死的结局,这一点和希腊思想有重大差别,可是它仍难免带着希腊思想的二元性
(注三八)。
我们不能否认,保罗既主张肉体的死乃是罪的结果,就等于将一种不十分合于整个圣经
以人为有限性的看法带到基督教的神学中。按照圣经的主要看法,死是表明那在上帝的
庄严,和人的软弱与人因被造而有依赖性之间的差别。这并不是说,肉身的死亡,即为
人的命运之最后决定。我们将于本书的下编讨论圣经中关于复活的盼望(注三九)。基
督教的那超乎现实生存的复活信仰,在理想上并不反对圣经的解释:这个现实世界在本
质上是善良而非邪恶的道理。保罗的观点即令有不符之处,但它的一般影响,乃是把古
典思想和基督教思想对现实世界的不同看法互混了。
基督教教义的另一特点是认为罪不是渊源于人的现实性,而是由人不愿意承认他自己生
存的有限性,这是基督教人性观中的第三因素,我们即将详加讨论。
附注:
注一、参考鲁宾孙(WheelerRobinson)的(TheChristianDoctrineofMan)第廿与
第六五面。同时参考(RealeucyklopaediefuerProtestantischeTheologieund
Kirche),第六卷第四五二面。
注二、同前第六卷,第四五三面。
注三、参看外士(Weiss)的HistoryofPrimitiveChristianity第二卷四七九面。霍
次满(Holtzmann)有同样的见解。但那个见解不是最后的,因为保罗在哥林多前书二章
十一节和五章三节上很明显地提到人的灵。
关于新约中“灵”(pneuma)一辞的详细解说,以及“灵”一辞在基督教思想中的定义
和含义,可参考贝芬(EdwynBevan)的SymbolismandBelief第七,八两章。
注四、女撒的贵钩利对人之具有上帝的形像界说如下:“神格乃是心智与道,因为‘太
初有道’……人性也离心智与道不远;我们在我们自己身上见到言语(道)和理悟,那
即是模仿神的道与心智而来的”见贵氏的人之创造(OntheMakingofMan)第五章。
又说:“因此,灵魂在知识和理性的事物上,才能找着它的完全,凡不属于知识和理性
之事物,虽也可用灵魂之名称,但那不是真的灵魂,只是与灵魂一名称有关的一种生机
力而已”(前论第十五章)。这种柏拉图思想的主要含义都为贵钩利所充分提出:“一
切禽兽的特性,都与灵魂中的理性部分合在一起。忿怒,恐惧,以及在人心中一切与理
性相反的活动,都属于禽兽的特性。只有理性思想,所谓人生命中的上选,才为人具上
帝的形像之印证”(OntheSoulandonResurrection)。然而贵钩利在他的理性主义
的观点中,用下面的说法介绍了更具圣经思想的成分进去:“再者,上帝是爱和爱的源
头;……创造人性的主也将爱作了人的性格;……若是没有爱,则上帝的形像之整个烙
印都变了。”(人之创造第五章)。
俄利根的柏拉图思想将圣经中的人的灵肉一体的看法完全摧毁。人具有上帝的形像之
说,由他看来,乃是指那堕落了的属天之灵,这灵乃以肉体的生活来补偿他前一个世界
中的堕落。
在阿奎那的思想中,“上帝形像”概念的理智与圣经成分都混在一起,而以亚理斯多德
的思想占主要成分。他以为上帝的形像,“主要地是心智的本性”;“其次人所具有的
上帝形像也有附带的品质,例如人从人而出神从神而出;人的整个灵魂是存在于人的整
个身体也存在于每一部分里面,正如上帝之与整个世界的关系一样。”然而这一个看
法,并没有动摇他的坚持的理性主义,因此他向奥古斯丁的主张谓具有上帝的形像的是
人而非天使一说――挑战。他说,“我们必须承认,严格地说,天使较比世人更具有上
帝的形像,虽说在有些方面,人是更像上帝一些。”(见SummaTheologiae第一部,第
九三题,第三条。)
阿奎那认为“上帝的形像”,无非是人因顺服和敬爱上帝而与上帝相连结;他坚持说,
那形像不是属于人的原来本性,否则就不能因人的堕落而被摧毁。世人现在既没有这种
关系,那么它应该是一种超本性的天赋,是人于堕落时所丧失了的:“人原来之具有正
直,是因为他顺服上帝,所以一切下层功能都顺服理性,而身体顺服灵魂;第一个顺
服,乃是第二第三个顺服的原因。很清楚的,这个顺服不是由于本性,否则它在犯罪之
后,仍将保存。……因之,那使理性顺服上帝的最初顺服,不只是一个本性上的恩赐,
而是超乎本性的恩典之赐予。”同上第一部第九五题,第一条。
天主教的教义,认为有一种超乎本性之“额外恩赐”是在人堕落时所丧失了的,然而人
本性上的德性并未受损伤,这种说法是很混淆的。表面虽说堕落时人所丧失的是一种超
本性的德性,但那使人有这德性的才能,也就是那引他犯罪的“才能”,即是人的那超
越自我的精神。因之,在堕落之后,人的构造是改变了。在本质上,人变成为一种亚理
斯多德所说的理性的人。他虽具有天然德性之能,却因他陷于有限,这“能”就受了限
制。他缺欠永恒之能。然而他如果真缺乏永恒之能,他也就不会犯那归荣耀于自己的罪
了。
注五、加尔文指出奥古斯丁思想之渊深,在人性论上,他与早期教父的谬妄混淆之见不
同。他说:虽说希腊教父比别人更加越限地称赞人的意志能力,就中尤以屈梭多模
(Chrysostom)为甚,然而除奥古斯丁之外,这些教父的种种游移不定,变迁多端的说
法,对人性迄无定论。从他的遗着中,很难找出结论。(见加氏的基督教要义第二卷,
第二章,第四节)。
注六、见奥氏的约翰福音注解第二十三章,第十节。
注七、见奥氏的DeTrinitate第十四章,四节,六节。
注八、见忏悔录第十卷,七至十七节。
注九、见奥氏的约翰福音注解第二十三章第十节。
注十、见Deverareligione第三十九章第七十二节。
注十一、见Retractiones卷一,第一章第二节。
注十二、见SermonsonNewTestamentLessons117:3:50.
注十三、见SermononPsalm118:Sermon18:30.
注十四、值得重视的,巴德虽在神学思想上跟从奥古斯丁的传统系统,然而因为他有意
证明上帝对人的启示除了启示本身所创造的以外,实际上与世人无接触之点,所以他发
现奥氏关于人具有上帝的形像之定义是很不妥的,并加以严厉批评。参看Doctrineof
theWordofGod二八一面。
注十五、见基督教要义第一卷十五章,第三节。
注十六、同前第一卷第十五章八节。
注十七、同前第一卷第十五章三节。在同一章中,加氏顺着一些早期的见解,指出人的
直立行走,乃人具有上帝的形像之表现:“我承认人的外表既使他与禽兽有别,也提高
他使之近乎上帝;那些以下面的话来了解上帝的形像的,我亦不加反对:
芸芸生物不能言,
视线低垂向地仙,
惟人高瞻超象外,
昂首举目望云天。”
注十八、见路德的创世记注解。路德之界说上帝形像,常以世人当前的罪恶情况和上帝
的形像相对比。路德之为人堕落以前之种种神话式的完全景况所混淆,更甚于改教运动
中之其他神学家,虽说改教运动之一切神学家,都承认人堕落以前景况之历史性。但路
德却以他的想像来描绘人堕落以前的完美景况,且坚持说,不仅是包括心灵上的特别恩
赐,而且包括体格上的完美。他说,亚当“具有敏锐的目力胜过山猫,”“体力胜过狮
子与熊,能驾驭狮熊,像我们驾驭别的幼弱动物一样。”
注十九、均见路德的创世记注解第二,四,五各段。
注二十、见亥得革的SeinundZeit第四九面。
注二一、见席勒的DieStellungdesMenschenimKosmos第四六至四七面。席勒这句话
显然是说得太过了。爱迪生的技术智能,是靠一种抽象和概念的思想能力,这能力是从
一种能“使整个的时间和空间的宇宙,连同自我本身在内,作为知识对象”的更高能力
而来的。若非如此,则猴子就当在某种程度下达到了爱迪生的技术智能。人与猴子的能
力分别,不仅是多寡的分别,而是品质的分别。但席勒从与理性对立的立场上,来着重
“灵”的终极地位是对的。普通所谓理性并不包括灵,而灵则包括理性在内。
注二二、见EntwedenOder第二卷第一八二面。
注二三、关于基督观与基督教的人的自由观的关系一问题,将于本书下编第三章详细讨
论。
注二四、席勒对这一区别说明如下:“理性的问题约如下述,‘我手臂上有痛楚。它是
从那里来的,我要怎样把它除掉呢?’决定这一点是属于科学的事。但我也可用手臂上
的痛楚来想到世界是不免痛苦,忧愁和邪恶的。于是我要问:痛苦,忧愁和邪恶在本质
上到底是什么呢?万物生存的究竟是什么?如何而使这种痛苦成为可能呢?且不管我们
人的痛苦如何。”同前第六○面。
注二五、希伯来书所引的这段经文如下:“主阿,你起初立了地的根基,天也是你手所
造的。天地都要灭没,你却要长存。天地都要像衣服渐渐旧了。你要将天地卷起来,像
一件外衣,天地都改变了,惟有你不改变,你的年数没有穷尽”(来1:10-12)。这段
经文引自诗篇第一○二篇。诗篇上对于这个道理,曾作多种不同的说明。
注二六、奥古斯丁对于基督教创世论双方对立的观点,即认为被造的世界既是好的,也
是不能自立的那种说法,曾详加阐述:“我问这到底是什么道理呢?我问地,地回答
说,‘我不是造物的主’;一切在地上的万物都这样说。我问海和海深处的一切活物,
它的回答说:‘我们不是上帝,请向在我们上面的探求罢。’……我问太阳,日亮,星
晨,它们也说,‘难道我们是上帝么?’于是我回答一切围绕我的肉体者说,‘你们都
告诉我,你们不是上帝;请告诉我,祂是什么。’它们乃大声回答说:‘祂创造我
们。’关于我的上帝,我曾问了整个的宇宙,而它回答我的是,‘我不是上帝,上帝是
我的创造主。’”见忏悔录第十卷第九节。
注二七、奥古斯丁以下面的话,驳斥神秘主义认为人可以成神的说法:“我以为人总不
能达到与上帝平等的地位,即令人内心达到了最完全的圣洁,不,我认为这是不可能
的。凡坚持人的进步可以进到如此完全地步,以致可变成神的本体,与神一样的,应当
有更透澈一些的思想。我自己必须承认,我不相信这件事。”OnNatureandGrace,第
三十八章。
注二八、见祁氏的DieKrankheitzumTode第廿七面。
注二九、纥耳米提加(Hermetica)中的ThePoimandresi一书,对人的堕落,即有此
说。希腊思想对两性问题则采取柏拉图Symposium的意见。斐罗(Philo)以为具有性生
活的人类,不会是按照上帝的形像造的。参考铎德(C.H.Dodd)的TheBibleand
theGreeks第一六五面。
注三十、见TheDestinyofMan二九九面。
注三一、见人之创造第十八章。
注三二、见OntheSoulandtheResurrection。
注三三、见反异端论(TreatiseAgainstHeresies),卷四,第三八章,第四节。爱任
纽并非一个纯希腊思想者,但他的思想深受理性主义的护教论者的影响。
注三四、见Anti-PelatianWorks,第一卷一五○面。
注三五、智慧书上说:“上帝造人原为不朽的,只因为魔鬼的妒嫉,死亡才进入世界”
(第二章廿三至廿四节)。
注三六、创世记三章十七至十九节上说:“地必为你的缘故受咒诅,你必终身劳苦,才
能从地里得吃的。地必给你长出荆棘和蒺藜来,你也吃田间的菜蔬。你必汗流满面才得
糊口,直到你归了土;因为你是从土而出的,仍要归于尘土。”
注三七、见道成肉身论(DeincarnationeVerbiDei)第五段。
注三八、关于死是由罪而来的教义,虽有多种不同的说法,但却是基督教正统教义始终
一致的主张。爱任纽的说法是:“上帝藉着死以限制人的罪恶的范围,使人因死而终止
犯罪,因为罪由于肉身的消灭而告结束。死之所以临到世上,乃为叫人终止罪中的生
活,人既对罪死了,然后才对上帝活着。”见反异端第三卷,廿三章第六节。
女撒的贵钩利认为上帝造人,使人必死,乃因预知人将犯罪:“祂既知道在人的被造的
本性中有犯罪的倾向,且人因堕落不能与天使平等,却要与低一等的被造物为侣,因之
当上帝按自己的形像造人时,祂就加上一些理性外的成分――使人性中含有那不属理性
的属性。”见人之创造第廿一章。
阿奎那的说法是:“人身原来之不朽,不是因为它内在有什么不朽的能力,而是因为神
所赐予人的灵魂的超本性的力量,只要人的灵魂能顺从上帝,它就可以靠那力量,保守
身体,不至朽坏……这一个使身体不朽的能力,并非灵魂的天然所有,乃是一种恩赐。
人虽在免罪和分享荣耀的事上,恢复了那恩赐;而那因罪而丧失的身体不灭,却未被恢
复。”见SummaTheologiae第一卷第九十七题,第一条。
马丁路德对于这个问题的观点也相似:“若是亚当未犯罪的话,仍然是要过肉体的生
活,仍然是要饮食休息的;他仍然是要生长,增加体魄,并生育后嗣,直到上帝把他转
移到属灵的生活,那时就可以说,他不要再过天然的动物性生活了。……然而他仍将是
具有骨肉的人,而不是像天使般的纯粹属灵的。”CommentaryonGenesis第三卷第五,
七节。
注三九、见本书下编第九,十两章——
在这个地球上,我们确实只能带着痛苦的心情去爱,只能在苦难中去爱!
我们不能用别的方式去爱,为了爱,我甘愿忍受苦难。
我希望,我渴望流着眼泪只亲吻我离开的那个地球,
我不愿,也不肯在另一个地球上死而复生!——
陀斯妥耶夫斯基
※来源:·瀚海星云bbs.ustc.edu.cn·[FROM:210.45.75.14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