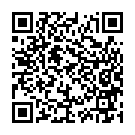首页 圣网读书 目录 A-AA+ 书签 朗读
启示的概念
第一节、启示的概念
人类试图完全了解上帝的性质和计划的努力最终是不成功的,这是多少年来基督教神学的一个重要主题。 尽管人们通常承认关于上帝的自然知识是存在的(卡尔·巴特的早期作品是这种共识的一个著名例外),但是其范围和深度都是有限的。 “启示”的思想表达了基督教的一个基本信念——我们需要“被告知上帝是什么样的”(云格尔,Eberhard Jüngel)。
20世纪60年代,基督教神学发生了一场巨变,许多传统思想受到挑战并被重新解释。 其中一个挑战针对的就是启示的思想。 当时出现了两种意见,每一种似乎都在招致对基督教传统中启示思想的怀疑。 首先,一些激进的作者提出,现代人对启示感兴趣并不是由于圣经本身,而是由现代哲学中的认识论问题引起的,比如,科学哲学中著名的关于“正确知识”的问题已经移转到了神学之中。 他们认为,圣经所关心的是拯救而不是知识,新约中的支配性问题是“我必须做什么才能得救”而不是“我必须知道什么”。 为了反对这种意见,人们指出,圣经中的启示经常用“知识”来表达,人的得救依赖于对在基督里获救的可能性的认识,而正确的回应是获得拯救的必要条件。 按照圣经来理解,“关于上帝的知识”并不仅仅是“关于上帝的信息”,而上帝在基督里的自我启示,是带来生命、赐予救恩的自我启示。
第二,一些圣经学者提出,启示对于旧约和新约都是不重要的。 他们提出,在圣经文本中启示的用语既不是基本的,也不是一致的。 但是,人们不久就发现,他们的分析根据是对已经被系统发展出来的“启示”思想不加批判的接受;而不是对圣经本身的启示用语的仔细思考。 当然,中世纪和现代的启示观念在旧约和新约里都找不到明确的陈述,这是事实。 但是,这绝不表示启示语汇在圣经中不存在或者不重要。
说新约没有将“启示”的含义视为“迄今未知的上帝的揭示”,这当然是正确的。 在其日常用法中,“启示”这个词意味着“使某事物在其完全意义上为人所知”或“迄今模糊不清的事物的完全显明”。 但是,在神学背景下说“上帝的启示”,并不意味着上帝的完全显明。 正如颇受尊敬的天主教神学家奥科林斯(Gerald O’Collins)所指出的:
在那些个性还没有完全暴露的人之间,启示也可能发生。 请看下面这句话:“他已经向我启示了他在这件事上的愿望”。 这个表达是不详尽的,也表明他们会继续进行沟通。 但是,一些东西已经暴露出来,而且其背景可以使人对另一个人的个性有所了解。 了解了其个性的某些内容不等于对其丝毫也不了解。 我们可以将“启示”在差不多同样的意义上用于上帝,可以谈论关于上帝的真实经验,这些经验传达了一些东西,但并没有将上帝完全地显明出来。
这里,奥科林斯表达了基督教神学的一个普遍共识。 例如,遵从东正教传统的许多作者强调,上帝的启示并没有取消上帝的奥秘。 纽曼(John Henry Newman)的“保留”教义强调了同样的观点。 对于上帝,我们所不知道的,总是多于他已经决定让我们知道的。 路德也提出,我们只能部分地了解上帝,但是,这些启示虽然只是一部分,却是可靠的、足够的。 路德逐渐提出了“上帝隐秘的启示”这一思想来说明这一观点。 这是他的“十字架神学”的重要内容。
大自然(或被造物)是其创造者——上帝的一个见证,这是基督教神学的一个共识。 然而,启示补充了关于上帝的这些普通知识,可以使我们获得通过其他方式不能得到的信息。 但是,启示思想的意义并不仅仅是传递关于上帝的知识,也是对上帝自己的揭示。 在谈论他人时,我们可以清楚地区分开“知道某人”和“认识某人”。 前者说的是大脑中的知识,或者是关于这个人的数据积累(比如他的身高、体重等);后者讲的则是个人关系。
在其高级意义上,“启示”并不只是知识的传播,它也是上帝在历史中对自己所做的揭示。 在其自我揭示过程中,上帝采取了主动,拿撒勒人耶稣的事迹是这一揭示过程的高潮和完成。 在20世纪,一些受到各种人格主义哲学影响的作家强调了这个观点,比如戈加登(Friedrick Gogarden)、朋霍费尔(Dietrich Bonhoeffer)和赫希(Emanuel Hirsch)。 布龙纳(Emil Brunner)也是这些思想家中的一员,他强调了道成肉身教义对启示的重要性:在基督里可以看到上帝对自己的自我揭示,上帝的启示采取了人格的形式。 在思考人格化上帝这一思想时,我们再来深入地讨论这个问题。
这里,我们来思考一个相关的有趣问题。 从大自然可以了解到上帝的哪些性质? 这个问题开启了一个通常称为“自然神学”的基督教思想领域,现在我们就来对其进行一些思考。
自然神学:其范围和局限
圣经作者意识到上帝在大自然中以某种方式启示他的尊荣与奇妙,如果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就不能理解圣经。 “诸天述说上帝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 (诗19:1)创造的教义是关于上帝的自然知识的基础。 如果是上帝创造了世界,那么在他的创造物中就可以找到上帝特殊作品的痕迹。 正如艺术家与众不同的风格是其雕塑的证据,或者画家会在他的作品上签上他的名字,上帝的临在也是这样,在其创造物中可以找到。 那么,在其哪部分创造物中可以找到呢? 在数个世纪的基督教神学所提供的相当多的答案中,可以挑选出三个答案:
1. 人的理性。 希坡的奥古斯丁在《论三位一体》中比较详细地讨论了这个问题。 他的论证可以概括如下。 如果上帝确实可以在其创造物中被认识,那么我们应该可以在其创造的顶点中发现上帝。 奥古斯丁(根据创世记2-3)认为,人性是上帝创造的顶点。 并且,根据他从其文化环境中所继承的新柏拉图主义的假设,奥古斯丁进一步论证说,人的推理能力是人性的顶点。 因此,他得出结论,在人的理性思考过程中,我们应该可以发现上帝的踪迹(或者更准确地说,是“三位一体的痕迹”)。
2. 世界的秩序。 现在,我们来看看托马斯·阿奎那关于上帝存在的重要论说。 其根据是,人们感知到大自然具有秩序,并且这个秩序要求人们对其做出解释。 同样地,人的心灵可以认识和研究大自然的这种秩序,这是一个事实,它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 人性中似乎存在一些东西,促使人们对世界追根问底;而且,世界中似乎也存在一些东西,对这些问题可以给出答案。 著名的理论物理学家和基督教护教者波金霍恩(John Polkinghorne)对这一点做出了如下评论:
我们可以理解这个世界,这是一个事实,对此我们是如此熟悉,所以大多数时候我们都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 这也是科学的前提条件。 但是,事情完全可以是另外一番情景。 宇宙曾经可能是完全无序的混沌,而不是一个有序的宇宙。 或者,宇宙可能具有合理性,但却不让我们认识它……在我们的心灵与宇宙之间,我们经验到的合理性与在外面所发现的合理性之间,存在着一致性。
我们的心灵中所出现的合理性与我们在世界中所发现的合理性(即秩序性)之间,存在着深层的一致性。 因此,纯数学这一抽象结构(这是人的头脑自由想像的结果)为我们理解世界提供了重要线索。 波金霍恩争论说,所有这些都是某种形式的自然神学,是在为基督教启示的完全知识预备道路。
3. 世界的美。 许多神学家形成自然神学观点根据的是沉思世界时所产生的美感。 例如20世纪作家巴尔塔萨(Hans Urs von Balthasar),他强调了美在神学中的重要性。 但是,对这一主题做出最有力研究的,也许当属著名的美国神学家爱德华兹(Jonathan Edwards)。 在其《个人叙述》一书中,他写下了他“单单仰望上帝之美”时的感受:
我走在那里,仰望天空和云朵,对上帝荣耀庄严和优美的感受在我心中油然而生,如此的甜美,我不知道如何来表达。 我似乎看见,万物都美好地关联在一起……那是美好、温和、神圣的庄严,也是庄严的温柔。
这种审美的迷醉感弥漫在爱德华兹的自传作品中,特别是在他的《杂记》一书中。 爱德华兹说,“开满鲜花的草地、柔和的微风会使我们感到欣喜,这时候”我们经验到的美感就是上帝神圣性的宣告,圣经阐明和证实着这种宣告,是这种宣告的可靠神学根据。
许多基督教神学家试图描述人们是如何透过自然认识上帝的,以上这些一掠而过所说明的只是其中的几种而已。
然而,透过大自然可以在多大程度上认识上帝? 这个问题在基督教作家之间引起了一些激烈的争议。 其中最有趣的一个争议发生在1934年。 下面我们就来讨论这一争议。
巴特——布龙纳争论
1934年,瑞士神学家布龙纳出版了一本书,题目是《自然与恩典》(Nature and Grace)。 在这部著作中,他认为,“我们这一代神学家的任务就是要找到一条回归到合理的自然神学的道路。” 在创造的教义中,特别是在人是照着“上帝的形像”造的这一思想中,布龙纳找到了其思想的线索。 人性的构成具有与上帝的存在类似的一面。 虽然人性之中含有罪性,但仍然具有认识上帝的能力。 有罪的人类仍然能够在大自然和历史事件中认识上帝,而且可以在上帝面前认识到自己的罪。 所以说,在上帝的启示与人性之间有一个“接触点”。
实际上,布龙纳是在说,人性当中已经有了一个现成的地方用来接受上帝的启示。 启示是在向人性说话,而人性本已具有了启示的某些思想。 例如,福音要求人们“悔罪”。 布龙纳认为,除非人类已经具有了关于“罪”是什么的一些思想,这种要求就几乎没有意义。 因此,福音的悔改要求的对象是至少已经知道一些“罪”、“悔改”的意思的听众。 启示同时带来了对罪的含义更为充分的理解,但同时也增大了人们已经存在的罪意识。
布龙纳的同乡卡尔·巴特愤怒地回击了这种思想。 他发表了对布龙纳的回击,这导致了他们多年友谊的破裂。 巴特的回击所使用的题目是宗教出版史上最短的题目之一,是德语词“Nein!” ,意思是“不!” 对于布龙纳对自然神学所采取的积极评价,巴特坚决地说“不!” 布龙纳似乎在说上帝需要人的帮助才能为人所知,或者在启示这件事上人类是在以某种方式与上帝合作。 巴特愤怒地反驳道:“除了同一位圣灵所建立的接触点,圣灵……不需要任何其他的接触点”。 在巴特看来,在人性中并不存在与生俱来的“接触点”,任何这样的“接触点”本身都是上帝启示的结果,是上帝的道所导致的,而不是人性的永久特征。
这个争论背后有一件事是人们特别容易忽略的。 巴特一布龙纳争论发生在1934年,希特勒在德国上台就是在这一年。 “创造的次序”这种思想是布龙纳论点的基础,这种思想可以追溯到路德。 路德认为,上帝为了防止世界陷入混乱,深谋远虑地在被造物中建立了某种“次序”。 这些次序包括家庭、教会和国家。 (德国路德宗认为教会和国家是亲密的联盟,正是这种思想的反应。 )19世纪德国新教自由派吸收了这种思想,并逐渐形成了一种重要的神学。 这种神学承认德国文化,包括对国家的积极评价。 布龙纳为使国家成为上帝的模型提供了根据,虽然布龙纳可能没有意识到,可是这引起了巴特的关切。 谁愿意希特勒成为上帝的模型呢?
我们已经比较仔细地探讨了启示的概念,现在我们就来看看基督徒对启示的来源的理解,其中最重要的来源是圣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