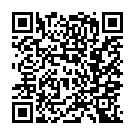首页 圣网读书 目录 A-AA+ 书签 朗读
基督教的上帝论
第一节、基督教的上帝论
基督教肯定上帝是存在的。 但是哪一位上帝呢? 这位上帝是什么样的呢? 基督教的信经不仅陈述了上帝存在这一信念,而且开始阐发基督教对这位上帝的属性和品格的独特理解。 特别重要的是,基督教断言上帝通过耶稣才能被认识。 我们已经看到,在耶稣其人及其作为中上帝将自己启示出来,这是基督教最重要的基本思想之一。
上帝是父
使徒信经开头即宣称“我信父上帝”。 这句陈述旨在说明,基督徒所相信的是一位有位格的上帝,而不是一个抽象的无位格的理念。 从旧约和新约关于上帝的用词中,可以清楚地知道这一点。 例如,二者在描绘上帝的属性和品格时,都使用了极为人格化的语言。 上帝可以被说成是“信实的”和“慈爱的”(这些词汇直接意味着一种个人关系)。 许多基督教作家指出,祷告者模仿了小孩子和父母的关系。 祷告表达了一种亲切的关系,即“对一有位格的对象的单纯信赖,他为我们所做的一切表明他完全值得信赖”(欧曼,John Oman)。 而且,保罗关于耶稣死于十字架上的后果的一个最重要思想就是,这带来了“和好”。 这一深刻的神学思想显然模仿了人类的人际关系。 它意味着上帝与罪人的关系,因着信,发生了改变,就像两个人(或许是疏离的丈夫和妻子)重新和好一样。
称上帝为“父”,就是肯定自己所相信的是一位有位格的充满活力的神,而不是一种无位格的静止的神圣力量。 但是其含义远不止这些。 例如,它还意味着我们来源于上帝,上帝关心我们就像父亲关心孩子一样。
中世纪杰出的基督教神学家托马斯·阿奎那认为,“上帝是父”这一比喻应理解为“上帝像人的父亲”。 也就是说,可以将上帝比拟为父亲。 在某些方面上帝与父亲相似,在某些方面则不然。 二者具有真正的相似性。 上帝关心我们,正如父亲关心他的孩子一样(见太7:7-11)。 上帝是我们存在的最终来源,正如我们的父亲生育了我们一样。 上帝像父亲一样对我们行使权威。 同样地,二者也具有真正的不同之处。 比如,上帝不是人类。
阿奎那想说的话非常清楚。 在与我们的日常生活联系在一起的形象和观念中,上帝将他自己向我们启示出来。 但是,这并没有将上帝降低为世俗世界的存在。 说“上帝是我们的父”并不等于说上帝仅仅是我们的又一位血缘意义上的父亲;而是说,思考我们的生父有助于我们认识上帝。 二者是一种类比关系。 像所有的类比一样,二者在许多方面是不同的。 然而,这仍然是非常生动有益的思考上帝的方式,使我们可以用我们所熟悉的世俗世界的词汇和形象来描绘最终超越俗世的事物。
圣经用来描写上帝的范型具有坚固的现实生活基础。 正如耶稣使用存在于现实生活的比喻来阐述神学观点一样,圣经作者们使用来源于古代巴基斯坦地区现实生活的范型来说明上帝的属性和意愿。 因为当时社会是男性统治的,所以用来描写上帝的范型多为男性。 例如,只能用父亲、法官或国王之类的男性形象来表现上帝的权威这一观念。 然而,圣经中也使用了其他范型。 例如,上帝经常被比作(无性别的)磐石,用来表达力量、稳固、持久等观念。 女性形象多用于描绘上帝对其子民的关心和同情,这常常被比作母亲对孩子的爱。 然而,重要的不是这些比喻,而是所谈论的上帝的性情。
圣经断言,古代以色列社会的国王、牧者、父亲形象可以作为上帝的合适范型。 但是,使用这些男性范型并不是说上帝是男性。 同样地,使用无性别的范型(比如磐石)也并不是说上帝是无性别的,使用女性范型(比如母亲)也并不是说上帝是女性。 把上帝说成是一位父亲,就是说,在古代以色列社会父亲所起的作用有助于我们对上帝本性的了解;这不是说上帝真的是一个男人。 圣经没有说上帝具有任何性别特征,无论是男性还是女性。 性别特征是被造物的一种属性,我们不能假定任何一种性别特征对应于上帝。
由于异教之神常常与性功能紧密联系在一起,所以旧约避免这种联系。 迦南生殖崇拜既强调男神的性功能,也强调女神的性功能;而旧约不认可神的性别或性功能是重要的这种观念。 并不需要回到异教的男神和女神观念,才能恢复这一观念:上帝既不是男性也不是女性;这些观念已牢固地根植于旧约和新约之中。
在本章的后面部分,我们会对上帝是创造者这一观念进行探讨,在刚才的讨论中对此已有所提及。 现在,我们来关注一个更具挑战性的教义——三位一体教义。
三位一体的上帝
三位一体教义是最具特色的基督教教义之一,也是最难理解的教义之一。 下面我们试图勾勒一幅三位一体教义主要特征的轮廓。 新约中并没有对这一教义的明确教导。 有两个段落确实指向对上帝的三位一体解释,那就是马太福音28:19和哥林多后书13:14。
这是新约对三位一体的暗示吗?
马太福音28:18-20
耶稣进前来,对他们(门徒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 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作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 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
哥林多后书13:14
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常与你们众人同在!
上面所引述的两段经文已深深扎根于基督徒的共识之中。 因为前者与受洗有关系,而后者在基督徒的祷告和献身时作为通用的形式来使用。 然而,无论是合在一起还是分开来看,都很难说这两节经文已经构成了三位一体教义。
三位一体教义的圣经基础并不是这两节经文,而是新约所见证的上帝遍在的活动模式。 父神是通过圣灵在基督里将他自己向世人启示出来的。 在新约作品中,圣父、圣子、圣灵具有最紧密的关系。 一次又一次地,新约段落将三者联系在一起,看作是一个更大的整体。 作为一个整体的上帝拯救的临在和大能,似乎只有同时包含这三者,才能表达出来(例子参见林前12:4-6;林后1:21-2;加4:6;弗2:20-22;帖后2:13-14;多3:4-6;彼前1:2)。
在旧约中也可以看到同样的三位一体结构。 其中可以识别出上帝的三个主要“化身”(personifications),它们天然地导向三位一体的基督教教义。 这三个“化身”是:
1. 智慧。 在箴言、约伯记、传道书等智慧书中,上帝的这个化身特别明显。 智慧这一上帝的属性在这里被看作像是一个人(因此产生了“化身”观念),是一个与上帝分开又依赖于上帝的存在物。 智慧(顺便提一下,它总是被当作女性)被描绘为创造中的积极力量,智慧在创世时留下她的印迹(参见箴1:20-23;箴9:1-6;伯28;传2:4)。
2. 上帝的话。 这里,上帝的言辞被看作是一个实体,是一个既独立于上帝、又来源于上帝的存在物。 在这些描写中,上帝的话来到世界上,带着上帝的意志和意愿,与男人和女人相遇,带来指导、审判和拯救(参见诗119:89;诗147:15-20;赛55:10-11)。
3. 上帝的灵。 旧约用“上帝的灵”这一短语来指称上帝在创世时的临在和大能。 这灵会在将要来的弥赛亚身上出现(以赛亚书42:1-3),在旧秩序最终结束时作为新创造活动的代理人出现(结36:26;结37:1-14)。
上帝的这三个“位格”(这里用希腊词hypostatization代替英语词“化身”)并不等于严格意义上的三位一体教义。 确切地说,这三个“位格”指向上帝临在和活动的模式,这个模式是无所不在、超越的上帝在创造活动之中并通过创造活动表现出来的。 上帝一位论的上帝概念不足以涵盖这种对上帝的动态理解。 三位一体教义所表达的正是上帝活动的这种动态模式。
上帝的行为模式在圣经和基督徒的经验之中启示出来,人们持续不断地对此进行判断性思考。 三位一体教义可以看作是这一思考过程的结果。 这并不是说圣经中包含了三位一体教义;而是说,圣经是那位要求人们以三位一体方式来理解的上帝的见证。
三位一体教义的发展与基督教对耶稣身份和意义的理解的发展有机地联系在一起。 耶稣与上帝“本体相同”(其希腊词为homoousios),而不是“本体相似”(其希腊词为homoiousios),这个共识在基督徒中越来越明确。 可是,如果耶稣是上帝,这对上帝意味着什么呢? 如果耶稣是上帝,那么不是有两个上帝了吗? 或者,是否应当对上帝的属性进行彻底的重新思考呢? 从历史发展来看,三位一体教义与基督的神性教义的发展密切相关。 教会越强调基督是上帝,人们要求其澄清基督与上帝关系的压力就越大。
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基督徒思考三位一体的起点是新约对上帝的临在和行为的见证,上帝的临在和行为是在基督里通过圣灵进行的。 爱任纽认为,救赎的整个过程自始至终都见证着圣父、圣子、圣灵的行为。 爱任纽使用了一个名词——“救赎组织”(the economy of salvation),这个名词在下面对三位一体的讨论中起着显著的作用。 “组织”(economy)这个词需要进行澄清。 其希腊词是oikonomia,基本含义是“治家的规则”(由此我们可以看出这个词的现代含义与其原意的关系)。 在爱任纽看来,“救赎组织”的含义是“上帝在人类历史中救赎人类的方式”。
当时,爱任纽面临着来自诺斯替派批评者的巨大压力。 他们主张,创造者上帝完全不同于(并且优越于! )救赎者上帝。 马西安所偏爱的诺斯替思想认为:旧约上帝是一个创造者,完全不同于新约中的救赎者上帝;因此,基督徒应当回避旧约,应当将注意力集中于新约。 爱任纽有力地反驳了这一思想。 他强调,整个救赎过程——从创世的那一刻起到人类历史的最后一刻——自始至终都是一位并且是同一位上帝的作为。 只存在惟一的救赎计划,在其中作工救赎其创造物的就是那一位上帝——他既是创造者也是救赎者。
爱任纽在其作品《对使徒布道的说明》(Demonstration of the Preaching of the Apostles)中强调,圣父、圣子、圣灵在救赎计划中发挥了既相互区别又相互联系的作用。 他这样宣告其信仰:
父神上帝是非受造的,是不能被包含的,是不可见的一位神,是宇宙的创造者……还有上帝的道,即上帝的独生子,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无时不在,集万事万物于一身,取了人的样式来到人间,……败坏了死权,带来了生命,恢复了上帝与人类的关系……还有圣灵……以新的方式向我们人类浇灌下来,在全地更新我们,使我们可以接近上帝。
这段话清楚地阐明了救赎三一论(economic Trinity),就是说,这是将上帝的属性理解为每一位格负责救赎计划的一个方面。 三位一体教义决非毫无意义的神学冥想,它直接以基督徒在基督里得救赎的复杂经验为根据,旨在对这些经验做出解释。
证据表明,到公元4世纪后半叶,关于圣父与圣子关系的争论已经得到了解决。 圣父与圣子是“一体的”,这一认识解决了阿里乌争论,在教会中建立了对圣子神性的共识。 但是,还有更加深入的神学建构需要完成。 圣灵与圣父、圣子的关系如何? 在上帝中圣灵不能被忽略,这在人们中间已经成为了一个日益增长的共识。 卡帕多西亚教父,特别是凯撒利亚的巴西尔(Basil of Caesarea),极其有力地捍卫了圣灵的神性,为三位一体神学最后成形奠定了基础。 现在,对圣父、圣子、圣灵的神性和同等地位已经形成了共识,剩下的就是发展出三位一体的模型,形象地表达我们对上帝的这种理解。
一般而言,东方神学倾向于强调三个位格的个性区别,同时强调圣子和圣灵皆来源于圣父以捍卫三者的同一。 三个位格的关系取决于三者各自是什么,所以圣子与圣父的关系被定义为“受生”和“是子”的关系。 奥古斯丁采取的不是这种思路,他更喜欢从关系的角度来看待三个位格之间的关系。 从而,西方神学从上帝这个统一体出发的倾向更加明显,在论述启示和救赎工作时尤其如此;同时倾向于用三个位格的相交来解释他们之间的关系。
东方神学的思路似乎在暗示,三位一体由处理不同事务的三个独立代理人组成。 后来的两个发展排除了这种可能性。 这两个发展通常称为“相融互摄”(perichoresis)和“运用论”(appropriation)。 尽管这些思想在三位一体教义发展的晚期阶段得到了充分发展,但是,在此之前,爱任纽和德尔图良的作品对这些思想无疑已有所暗示,尼撒的格列高利的作品则对这些思想进行了更加充实的表述。 现在我们就对这两个思想进行一些探讨,这会对我们有所裨益。
1. 相融互摄。 其希腊原词为perichoresis,在公元6世纪时已普遍使用。 我们经常可以遇到这个希腊词的拉丁语形式(circumincessio)和英语形式(“mutual interpenetration”)。 “相融互摄”指的是三位一体的三个位格相互联系的方式。 这个观念承认每一个位格的独特性,同时强调每一个位格都分享其他两个位格的生命。 “一个存在共同体”这个比喻经常用来表达这一思想。 在这个存在共同体中,每一个位格都保持着其独特身份,同时又渗透到其他两个位格之中并被其他两个位格所渗透。
2. 运用论。 形态论异端认为,在救赎计划的不同时刻,上帝以不同的“存在形态”存在。 所以,在一个时刻,上帝以圣父的形态存在,创造了世界;在另一时刻,上帝以圣子的形态存在,救赎了世界。 运用论教义强调,三位一体的工作是一体的;每一个位格都参与了上帝的每一个外在行为。 所以说,圣父、圣子、圣灵都参与了创造工作,不能认为创造只是圣父自己的工作。 例如,希坡的奥古斯丁指出,创世记的创世叙述中谈到了上帝、上帝的话和上帝的灵(创1:1-3),这显示,在救赎史的这一关键时刻,三位一体的三个位格全部在场并且都在起作用。
但是,这种想法是正确的:创造是圣父的工作。 虽然事实上三位一体的全部三个位格都参与了创造活动,但是认为创造是圣父的独特行为是适当的。 同样地,整个三位一体都参与了救赎工作,但这种说法也是正确的:救赎是圣子的独特作为。
相融互摄和运用论教义合在一起,让我们想到,上帝是一个“存在共同体”,在其中所有一切都是共享的、合一的、相互交流的。 圣父、圣子、圣灵并不是像跨国公司的三个子公司那样是一位上帝的三个孤立的、分离的部分。 更恰当地说,他们是同一位上帝之中的三个分别,在救赎计划和人类对于救赎、恩典的经验之中显明出来。 三位一体教义断言,在救赎史复杂的表面之下,在我们对上帝的经验之中,有一位上帝存在,并且只有一位上帝存在。
在整个罗马帝国(无论东方还是西方),人们对尼西亚信经达成了共识,这是早期教会历史中最重要的事件之一。 在教会历史上至关重要的时期,这个文件旨在为教会提供教义的稳定性。 其中部分文本称圣灵是“从父而来”。 但是,到19世纪时,西方教会修改了这句话,通常说圣灵是“从父和子出来”。 从此,“和子”(filioque)这个拉丁词逐渐地用来指称这些增加的内容及其所表达的神学思想,现在已为西方教会广泛接受。 当时,圣灵的“双重来源”思想令希腊基督徒极为愤怒。 这不仅给他们带来了严重的神学问题,而且篡改了神圣不可侵犯的信经。 许多学者认为,正是这种恶感导致了发生在大约1054年的东西方教会的分裂。
“和子”争论特别重要。 无论是作为神学问题本身,还是作为目前东西方教会关系中的重要因素,都很重要。 因此我们想对此问题进行一些详细的探讨。 关键的基本问题是,圣灵是只从父自己出来还是从父和子出来。 前者是东方教会的立场,卡帕多西亚教父们的作品表达得最为充分;后者是西方教会的立场,奥古斯丁是其代表人物。
希腊教父们强调,在三位一体中只有一个来源。 父神是所有一切——包括三位一体中的圣子和圣灵——的惟一的、至高无上的来源。 子与灵皆来源于父,只是方式不同。 神学家们不停地寻找合适的词汇来表达这种关系,最后确定了两个区别很大的比喻:圣子是从圣父“受生的”(begotten),而圣灵是从圣父“出来的”(proceed)。 这两个词想表达的意思是:圣子和圣灵皆由圣父产生,但产生的方式不同。 用来表达这种区别的两个英文词是笨拙的,这反映了如下事实:所涉及的两个希腊词(gennesis和ekporeusis)很难用现代英语来翻译。
为了帮助人们理解这个复杂的过程,希腊教父们使用了两个比喻。 父神说出他的话;同时呼出这些话,父神之所以呼出,为的是这些话能够被听见、被接受。 这里所用的比喻以圣经传统为其坚实的根据。 圣经传统认为,圣子是上帝的话,而圣灵是上帝的呼出。 这里,一个显而易见的问题出现了:卡帕多西亚教父和其他希腊作家为什么要花费如此之多的时间和精力阐述圣子和圣灵的这些区别呢? 答案非常重要:对圣子和圣灵来源于圣父的方式,如果不做出区分,得出的结论将是——上帝有两个儿子,那就会产生无法解决的问题。
在这种背景下,圣灵来自于圣父和圣子这种观点是难以想像的。 为什么这样说呢? 因为这会彻底损害如下原则:圣父是所有神性的惟一来源和出处。 这等于是说,在一位上帝之内神性的来源却有两个,上帝内部存在矛盾和紧张。 如果说圣子分享了圣父所独有的作为神性来源的能力,那么该能力就不再是独有的了。 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希腊教会认为,西方教会关于圣灵具有“双重来源”的想法完全不可信。
但是,奥古斯丁认为,我们必须坚持圣灵从圣子出来。 这种想法的主要证据之一是约翰福音20:22,其中讲到复活的基督向门徒吹气,并且说:“你们受圣灵”。 奥古斯丁专门详细阐述了上帝的内在关系的思想,认为三位一体的三个位格应当用彼此之间的关系来定义。 所以,圣灵被看作是圣父与圣子之间的爱和亲密关系。 奥古斯丁相信,第四福音书所描述的圣父与圣子在意愿和目的上的同一,正是以这种关系为基础的。
下面,我们可以对这两种思路的基本区别做出一些概括。 希腊思路的目的是捍卫圣父是神性的惟一来源这一独特立场。 所以说圣子和圣灵皆来源于圣父,方式虽然不同,但同样有效。 这个观点反过来也捍卫了圣子和圣灵的神性。 在希腊人看来,拉丁思路似乎在上帝之内引入了神性的两个独立来源,削弱了圣子和圣灵的重大区别。 希腊人认为圣子和圣灵具有截然不同而又相互补充的作用,西方传统则认为圣灵是基督的灵。 确实,继承希腊传统的许多现代作家已经对西方思路提出了批评,比如俄罗斯作家洛斯基(Vladimir Lossky)。 在其论文“圣灵的来源”中,洛斯基认为西方思路必然地会导致圣灵非位格化,导致错误地强调基督其人及其作为,会将上帝简化成一个非位格的原则。
拉丁思路的目的在于保证圣子与圣灵具有足够的区别,同时又显示出其相互联系。 对“位格”所采取的强烈关系色彩的思路必然会导致对圣灵的这种看法。 后期拉丁作家对希腊立场非常敏感,他们强调,自己的思路并没有在上帝之中预设神性具有两个来源。 里昂公会议做出了这样的陈述:“圣灵出自于圣父和圣子,却不是出自两个来源,而是出自同一个来源”。 但是,这个教义仍然是引起争论的一个根源,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得到解决。
��